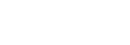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反避稅政策體系研究
一、現有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稅收政策體系
我國個人所得稅法體系有專門針對自然人股權轉讓涉稅行為的管理辦法,但該辦法適用范圍僅限于自然人股東轉讓中國境內成立的企業或組織(不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的股權或股份。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沒有專門的管理辦法。實踐中,主要依據國內法、稅收協定(安排)的相關條款,以及一些規范性文件劃分稅收管轄權,并進行規范。(一)國內法和稅收協定(安排)層級不同效應互補
國內法可對一些所得的征稅權進行創設,稅收協定(安排)主要針對某一項所得就締約國雙方的稅收管轄權進行劃分。
目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所得稅政策體系主要由三個層級構成。第一個層級是國內法和行政法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境外股權轉讓所得屬于個人所得稅九類所得項目之一的財產轉讓所得,其征稅權來源于此。第二個層級是相關稅收協定(安排)。目前,在我國和103個國家(地區)簽訂的已生效稅收協定(安排)中,部分協定(安排)通過“財產收益”章節對締約國一方居民轉讓締約國另一方財產涉及的征稅權進行了劃分:一是考察對方居民所轉讓公司股權價值是否主要由位于我國境內不動產構成;二是考察對方居民轉讓股權前十二個月內是否直接或間接參與我國境內公司25%以上資本。第三個層級是規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征收個人所得稅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國稅發〔1994〕89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及議定書條文解釋》(國稅發〔2010〕75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稅收協定中財產收益條款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59號)、《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居住時間判定標準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19年第34號,以下簡稱“34號公告”)以及《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境外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20年第3號,以下簡稱“3號公告”)等,對稅收居民身份和住所的判定、所得來源地的規定以及相關協定中財產轉讓所得條款的執行口徑等問題進行了規范。
(二)居民和非居民身份不同政策相異
自然人取得來源于中國境外股權轉讓所得,其納稅義務的判定需要綜合考慮在華是否有住所、在華累計居住天數等與其稅收居民身份判定有關的因素,在復雜情況下(如構成雙方稅收居民)還需利用加比規則,進一步考察其重要利益中心、習慣性居住地以及國籍因素,直至稅務當局按照雙方稅收協定相關條款啟動相互協商程序,以判定其最終居民身份歸屬,確定其最終納稅義務所在地。因此,納稅人具有哪種稅收居民身份直接影響其適用的稅收政策,決定其應負的納稅義務。
此外,居民納稅人取得境外股權轉讓所得時,在中國境內是否有住所,也會產生不同的稅收結果。如在華有住所,則構成有住所稅收居民,其取得的境外股權轉讓所得應當按照“財產轉讓所得”單獨計算應納稅額,按3號公告中規定的稅收抵免規則抵免在境外已繳納稅額后,為其在華實際繳納稅額,向中國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如在華無住所,則其是否構成在**稅義務需先根據34號公告第一條的規定確定在華居住天數;如其股權轉讓行為發生所在納稅年度前六年的任一年在中國境內累計居住天數不滿183天或者單次離境超過30天,且該筆所得由境外單位或者個人支付,則可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如不符合上述條件則應向中國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
作為非居民,其僅就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境外股權轉讓所得在大多數情況下被認定為來源中國境外的所得,在中國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有兩種情況除外:一是根據3號公告第一條第七款的規定,境外被轉讓股權公允價值50%以上直接或間接來自于位于中國的不動產,符合此條件的境外股權轉讓所得將被直接認定為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應向中國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二是通過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被中國稅收機關進行納稅調整。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在第十三條第五款中約定,一方居民轉讓締約國另一方居民公司股權行為發生前十二個月內曾直接或間接參與該公司至少25%資本,可在該締約國另一方征稅。雖該轉讓行為一般是指非居民納稅人直接轉讓中國公司股權,但如果其通過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間接轉讓中國公司股權,則中國稅務機關有權啟動反避稅調查程序,進行反避稅調查。經歸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所得納稅義務詳見表1。

二、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主要避稅手段
巨額的稅收利益往往會驅動自然人在進行股權投資和轉讓之前進行稅收籌劃。轉讓人通常會綜合其自身稅收居民身份、企業組織形式、各國所得稅制度、稅收協定(安排)條款等各種因素進行統籌安排。另外,由于自然人交易較為隱蔽,當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避稅呈現手段多樣化、形式復雜化的特點。(一)利用境外殼公司間接轉讓境內企業股權
自然人通過在低稅率國家或地區設立殼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境內公司,通過轉讓境外殼公司股權的形式間接轉讓境內公司股權。居民納稅人和非居民納稅人均會采用此種形式。對居民納稅人而言,其通過轉讓境外殼公司間接轉讓境內企業股權,利用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不履行納稅申報義務,從而獲取不當稅收利益;對于非居民納稅人而言,其股權轉讓所得從形式上屬于來源于中國境外所得,中國沒有征稅權。此種避稅手段是自然人對境外股權轉讓所得進行避稅的一般操作,在此基礎上衍生了其他更為復雜隱蔽的避稅形式。
(二)所得囤積在境外個人控股公司中不作分配
在第一種避稅手段的基礎上,納稅人通常在境外避稅地設立多層復雜股權架構,形式上股權轉讓方為境外公司法人,但其控股方為個人。為避免因中國居民身份構成全球所得向中國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股權轉讓所得不直接分配給個人股東,而是長期囤積在境外個人控股公司賬戶中。居民個人通過此種手段取得的所得性質為股息紅利所得,而非財產轉讓所得。
(三)變更稅收居民身份逃避繳納稅款
此種手段指的是具有本國國籍的居民納稅人,通過變更國籍等方式改變其稅收居民身份。變更為非居民稅收身份后,該自然人取得的境外股權轉讓所得從形式上為來源于中國境外的所得,以此達到免予向中國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目的。
(四)利用關聯關系操縱股權轉讓對價
自然人作為股權轉讓方,與受讓方構成關聯方。雙方約定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股權轉讓對價,以減少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從而獲取不當稅收利益。
(五)濫用企業組織形式逃稅或獲取稅收協定(安排)優惠待遇
非居民個人在股權轉讓行為前的十二個月內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被轉讓公司25%的資本,由于其所在國(地區)和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安排)規定中國對其直接轉讓中國境內公司股權轉讓所得擁有征稅權,為避免直接轉讓中國境內公司股權產生納稅義務,其采取通過轉讓境外設立的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中間層公司股權的方式,以逃避繳納稅款或獲取稅收協定(安排)優惠待遇。
三、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體系需進一步完善目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所得納稅義務的底層規范主要來源于對“稅收居民”和所得來源地的相關規定,即主要解決要不要征稅的問題,但下一步如何征稅尚未有明確規定。
1.缺少完整的上位法支持
企業所得稅反避稅在政策和征管方面有明確的上位法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第六章和《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六條。《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六條的規范對象主要針對企業和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稅務機關有權進行納稅調整,其調整對象并未包括個人。而個人所得稅反避稅的上位法依據目前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尚未在《稅收征管法》中體現。
2.轉讓定價條款尚未明確
目前,個人所得稅相關法律法規暫未對“關聯方”“關聯交易”“獨立交易原則”等基本概念進行明確,相關闡述均來自《企業所得稅法》中特別納稅調整相關文件。《個人所得稅法》中的“關聯方”是否能直接借用基于企業所得稅法原理的界定,需要進一步探討。由于基本概念尚未明確,轉讓定價方法和調查調整也無從談起,這使稅務機關在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涉稅行為進行反避稅管理時面臨政策基礎的困境。
3.受控外國企業條款尚未明確
現有受控外國企業管理規定主要來自《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有關“控制”的定義、所得計算方法、日常管理規定以及豁免條款均基于《企業所得稅法》。而針對自然人個人所得稅法領域的受控外國企業管理規定則有待進一步明確。
4.一般反避稅條款尚未明確
針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行為的一般反避稅規則,需要進一步明確。首先,沒有列舉何種自然人避稅行為屬于一般反避稅管理的范疇;其次,尚未明確針對個人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的行為進行審核的具體內容和操作辦法。
5.相關規范性文件仍缺位
針對自然人境內股權轉讓和非居民企業間接股權轉讓,我國已出臺了較為完善的專門的規范性文件,并且管理手段也日趨完善。而針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缺少專門的規范性文件對各種轉讓形式的稅收問題的處理,包括對收入、原值計算以及征管配套措施等方面進行全面規范。現有的稅收政策體系已落后于日趨復雜的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避稅模式的發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非居民個人采用本文第一種避稅手段間接轉讓中國境內公司股權時,根據3號公告第一條規定,其取得的所得為“來源于境外所得”,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非居民個人僅就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非居民個人通過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轉讓境外股權,雖然轉讓價值主要來源于境內企業,境外企業無經濟實質,資產直接或間接由中國境內的投資構成,但其取得的境外股權轉讓所得在中國亦可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顯然,這不符合利潤應在價值創造地征稅的原則。
(二)征管機制亟待完善
1.管理部門職能有待理順
目前,在省級稅務機關層面,個人所得稅管理部門負責個人所得稅政策指導,國際稅務管理部門還具有外籍人員個人所得稅管理職能。一些設有反避稅專業局的省市,其反避稅調查職能歸口在反避稅調查局。究竟由哪個部門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進行反避稅管理仍需進一步研究和明確。
2.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
現有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更側重于日常管理,個人取得的境外股權轉讓收入主要在《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表(A表)》或《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表(B表)》進行申報。實踐中,如果自然人從主觀上對其境外股權轉讓收入進行瞞報,稅務機關往往因為缺少信息獲取渠道而很難發現。由于尚未建立境外股權轉讓報告制度和稅收籌劃方案強制披露制度,稅務機關獲取境外股權轉讓信息和稅收籌劃方案的渠道極其有限,很難對納稅人的稅收籌劃及時地進行識別和審核,難以對避稅安排進行有效規范。
3.懲戒機制不完善
在日常管理中,稅務機關對個人境外股權轉讓情況進行核實時,股權轉讓相關方或中介機構往往以各種理由拒絕提供信息或提供信息不充分。稅務機關對此缺乏有效的懲戒手段,難以有力制約納稅遵從度不高的納稅人。
4.國際協作力度有待加強
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所得的納稅主體為個人,其避稅手段和操作方式高度專業化,取得收入較為隱秘。同時,其轉讓行為主要集中在低稅率國家(地區),這些國家(地區)大多尚未和我國簽訂雙邊稅收協定(安排),稅收情報信息交換渠道不暢通,個人海外銀行信息的獲取存在客觀困難,征納雙方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涉案線索的收集困難重重。
四、相關建議
(一)進一步完善自然人反避稅政策體系1.完善《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相關規定
在現有《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六條的基礎上,增加既適用于企業又適用于自然人的反避稅原則性規定;加入一般反避稅條款,對“經濟實質”“合理商業目的”以及“實質重于形式”進行明確,并在實施細則中予以詳盡的闡述;引入稅收籌劃方案強制披露規則,強化籌劃信息獲取手段。為制定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反避稅規范性文件提供上位法支持。
2.細化個人所得稅反避稅條款
充分利用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研究成果,科學借鑒企業所得稅特別納稅調整的立法思路,結合個人所得稅稅制特點和管理實踐,對個人所得稅反避稅條款的基本概念進行明確和細化。出臺個人所得稅轉讓定價規則,完善適用于企業和自然人的受控外國企業管理辦法,規范個人所得稅一般反避稅管理范疇,明確針對自然人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的行為進行審核的具體內容和實施辦法。
3.加快出臺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規范性文件
借鑒境內個人股權轉讓和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境內財產的管理辦法,出臺針對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的規范性文件。對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關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7號,以下簡稱“7號公告”)。該公告根據一般反避稅規則,通過將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交易,重新定性為直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交易,進而征收企業所得稅。對于非居民個人通過轉讓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稅財產的境外企業股權而取得的所得,本文認為不應簡單按照3號公告相關規定定性為來源于境外所得,而應先進行合理商業目的判定。具體實現路徑可借鑒7號公告的相關理念,結合個人所得稅有關規定,通過考察該交易中被轉讓境外企業股權價值是否主要來源于境內企業、境外企業有無經濟實質、其資產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構成等要素,對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重新定性為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并將該所得定性為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實施反避稅調整。這既符合二十國集團(G20)稅改倡導的“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征稅”這一基本原則,也有利于維護我國稅收主權。
(二)強化自然人反避稅征管體系建設
1.建立境外股權轉讓報告制度
要求境外股權轉讓的轉讓方或被間接轉讓股權的中國居民企業及時向主管稅務機關報告股權轉讓事項并提交相應涉稅資料,由稅務機關將信息錄入核心征管系統,實現涉稅信息交叉比對和審核校驗。
2.進一步完善自然人納稅信用管理體系
將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是否履行報告和納稅義務納入自然人納稅信用管理體系。對于未履行報告和納稅義務而被特別納稅調整的,認定為失信行為,根據納稅信用管理制度實施失信懲戒。
3.研究建立自然人稅收籌劃方案強制披露規則
作為BEPS行動計劃的內容之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G20成員國中已有美國、英國、韓國等8個國家出臺了強制披露規則,并運行卓有成效。據統計,在美國、加拿大、愛爾蘭、南非、英國這5個實行強制披露規則的國家中,42%的惡意籌劃安排是通過報告義務發現的,稅務審計的識別效果則排在第二位。4為提高稅收透明度,在平衡征管成本和遵從負擔的基礎上,應辯證地吸收借鑒OECD關于強制披露機制設計的研究成果,在《稅收征管法》的修訂過程中引入強制披露規則,有效識別激進的稅收籌劃及其籌劃方案,把握好個人所得稅改革工作中關于充分發揮涉稅行業協會、機構專業化作用的導向和震懾惡意稅收籌劃的關系,出臺自然人稅收籌劃方案強制披露規范性文件。
(三)建立和完善反避稅組織架構
統籌建立能有效應對當前反避稅發展趨勢、對自然人和企業實施一體化管理的反避稅職能機構。盡快理順各相關部門和各管理層級的職責分工,形成對企業和自然人反避稅政策指導有力、日常管理到位、納稅服務優化、調查工作補位、運行高效的組織架構。
(四)加強所得稅反避稅人才隊伍建設
系統地開展個人所得稅和反避稅業務相結合的專業培訓,補齊現有反避稅人才的業務短板。進一步加強征管體制改革后業務和人員的融合,借鑒企業反避稅工作經驗,不斷提升自然人反避稅管理水平。培養一批既能熟練開展企業反避稅工作、又能適應自然人反避稅工作的高層次專業化人才。
(五)拓展反避稅國際協作體系
利用好《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等國際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加大稅收情報交換工作力度,進一步拓展我國國際稅收征管協助的廣度和深度;依托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機制(CRS),不斷完善CRS信息管理、分析工作以及CRS管理部門和反避稅調查部門之間信息溝通反饋制度,打擊自然人利用跨境金融賬戶逃避稅的行為。通過拓展反避稅國際協作,不斷擠壓自然人境外股權轉讓惡意稅收籌劃空間,維護我國稅收權益。
作 者 信 息
孔丹陽(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
宋春輝(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第三稅務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