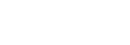持有多類資產的BVI公司就可以免受經濟實質法規制嗎?——一份IPO法律意見書引發的思考
近日,某擬上市公司IPO的法律意見書中,就BVI經濟實質法對發行人境外架構的影響進行了答復。[1]該答復主要援引了境外律師事務所的相關意見,認為發行人的相關BVI公司不屬于經濟實質法的規制范圍,不存在被處罰或注銷的風險,因此不會對發行人的控制權穩定性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主要理由摘錄如下:
第一,根據《經濟實質法》的規定,在任何財務年度從事“相關活動”的“法律實體”應當滿足關于“經濟實質”的要求。前述“相關活動”系指從事銀行業務、保險業務、基金管理業務、金融和租賃業務、總部業務、航運業務、控股業務、知識產權業務、分銷和服務中心業務等九類業務。
第二,因為發行人相關BVI公司持有美國政府債券,所以發行人相關BVI公司不會被認為從事“控股業務”。《經濟實質法》第 2 條規定的“控股業務”指純控股企業的業務,依據《經濟實質規則》 (the Rules on Economic Substance)第 5.25 款(及其注釋),“純控股企業”采用狹義定義,即只有當一個法律實體有且只持有產生股息或資本利得的股權時才符合“純控股企業”的定義。依據《經濟實質規則》第 5.27 款,擁有其他形式資產(比如有息債券、政府證券、不動產法定權益或受益權)的實體,不屬于“純控股企業”,不會被認為從事“控股業務”。
第三,發行人相關BVI公司亦未從事《經濟實質法案》規定的其他“相關活動”,因此不屬于《經濟實質法案》的規制范圍。
根據該意見書的答復,似乎會得出一個令人疑惑的初步結論,即BVI公司在僅持有公司股權的情形下需要進行“控股業務”的經濟實質測試,在此基礎上另行投資其他類型的資產(如政府債券、房產等)反而不再屬于從事“控股業務”,也無需接受“控股業務”的經濟測試,如果公司也未從事其他類型的“相關活動”,即可不再受《經濟實質法案》的約束。如果該初步結論能夠成立,未來其他擬上市公司存在BVI控股架構也能夠采取類似的方式免于《經濟實質法》的規制。這樣的理解是否合適?在其他稅務轄區的經濟實質法體系下是否也有類似的規避方式?
二、相關問題的分析
(一)經濟實質法的立法背景
在討論經濟實質法的具體規定時,必須站在規制有害稅制競爭的國際稅法背景予以審視,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釋,雖然這樣的解釋,未必與相關稅務轄區經濟實質法相關規則的文義,以及相關立法機關的立場完全相符。我們在以前的文章《避稅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評經濟實質法》中,已經對經濟實質法出臺的來龍去脈進行了較為系統的介紹,不再贅述。簡言之,經濟實質法項下的九類具體業務活動類型并非隨意列舉,而是有害稅制競爭論壇(FHTP)基于以往審查經驗的歸納與共識。
近些年,OECD意識到如果僅針對非避稅地進行有害稅制競爭審查,反而可能給避稅地帶來監管套利的機會。因此,2018年OECD在《考慮透明度與實質性因素,更有效地打擊有害稅收實踐(第五項行動計劃)》[2]的包容性框架下發布了新的報告——《恢復對不征稅或者名義征稅轄區應用實質性活動因素》[3](“《新報告》”)。各避稅地稅務轄區的經濟實質法立法所涉及的法律框架、相關構成要件以及法律后果,均應被視作是對BEPS第五項行動計劃以及《新報告》有關要求的具體實施。
(二)經濟實質法的規制路徑
1.經濟實質測試
考慮到遵循BEPS行動計劃要求的一致性,各避稅地稅務轄區的規制路徑也是類似的,即要求適格相關主體(relevant entity)在從事相關活動(relevant activity)時應當證明其符合經濟實質的要求。經濟實質的具體證明主要包括以下三類測試:
(1)決策與管理測試,即就相關業務以適當的方式在該稅務轄區進行了決策與管理;
(2)核心創收活動測試,即就相關活動取得的收入而言,存在核心創收活動。九類不同類型活動的核心創收活動在具體內容上存在差異。
(3)充足程度測試。即相關實體應當有充足數量的適格雇員,并且有從事該項活動成比例的運營支出以及物理存在(如辦公場所、設施等)。
2.合規遵從
非避稅地優惠稅制給予納稅人的不當稅收優惠可以要求納稅人返還,補征稅款,但是避稅地不征稅,因此需要建立一個嚴厲、有效、具有勸阻性的法律責任體系,足以震懾相關實體進行經濟實質法的稅收遵從。[4]這也是各避稅地轄區經濟實質法中相關合規遵從要求以及相應法律責任體系的由來。
(三)“控股業務”應如何進行經濟實質測試?
1.BPES報告層面:對控股公司進行區分要求
BEPS第五項行動計劃報告中[5],將稅務轄區實施的控股公司優惠制度(Holding company regimes)區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施加了不同的實質活動要求。這兩種控股公司類型分別為:
(1)為持有各種資產并取得多重類型收入(如利息、租金以及特許權使用費)的公司提供稅收優惠;
(2)僅針對持有股權投資而取得股息和財產收益的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對于第一種情形,如果要對控股公司獲得股息和財產收益以外的其他收入提供稅收優惠,應當要求符合條件的納稅人從事與其收入類型相關的核心業務活動。
對于第二種情形,即僅針對股息和財產收益給予優惠待遇的,通常會存在其他的政策考慮,例如緩解經濟雙重征稅問題。因此,可能并不會要求企業較深程度地實質性從事和控股與管理股權相關的主要活動。這種情形下,各國主要關心的往往涉及透明度以及無法確認股息受益所有人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已經通過其他制度得以部分解決,例如情報交換、防止協定濫用、混合錯配、受控外國公司制度等。

2.避稅地的立法實踐:對“控股業務”的限縮解釋
所有避稅地稅務轄區在經濟實質法立法中都規定了“控股業務”的情形。但是有趣的是,只有百慕大在立法中延續了BEPS第五項行動計劃報告項下關于“控股業務”經濟實質要求的完整邏輯,即將控股業務區分為純控股公司以及持有多種資產的公司兩種類型。[6]簡化經濟實質測試僅僅適用于純控股公司,對于持有多類資產的公司需要遵循完全的經濟實質測試。[7]
而BVI、開曼、阿聯酋等避稅地的經濟實質法中,徑直將“控股業務”限縮定義為純控股實體從事的業務。[8]同時,又進一步明確“純控股實體”為僅持有其他實體權益并且以取得股息或資本利得為唯一目的的實體。這些避稅地在其經濟實質法相關解釋規則中,進一步明確對該定義的概念進行限縮是有意為之,以限制簡化經濟實質測試的適用范圍。
例如BVI在其《經濟實質規則》第5.27條中明確,如果實體擁有其他類型的資產(例如債權、政府證券、不動產的法定或者受益權利)將明確不屬于純控股實體(即使其仍然持有權益投資),也將不被視為從事“控股業務”。當然5.29條也進一步規定,相關實體持有的資產不屬于權益投資不構成純控股實體,但仍然可能構成從事其他類型“相關活動”。值得指出的是,這里的構成其他類型“相關活動”,取決于相關實體當年度的具體經營情況,即該相關實體所從事的核心創收活動也是企業和BVI稅務機關判斷是否從事特定類型“相關活動”的重要依據,存在較大的解釋和適用空間。
從立法技術和應然角度考量,BVI等避稅地關于“控股業務”的規定是不周延的。一個控股公司持有多種類型資產,即使其中主要部分仍然是公司股權,根據現行規定竟然可以不構成“控股業務”,繼而免于滿足“控股業務”的經濟實質測試的要求。當然,即使如此,該控股公司仍然需要判斷其是否構成其他類型的“相關業務”,并接受所涉類型活動的經濟實質測試。這就可能出現題述案例的情形,當一個公司持有公司股權之外持有部分其他類型的資產(如政府債券、不動產等),將不構成經濟實質法項下的從事“相關活動”,也將不必要按照經濟實質法的要求滿足經濟實質測試。
一個可能的猜測是,BVI等避稅地的這一做法,一方面是考慮到“控股業務”并非有害稅制競爭的規制重點,對“控股業務”做適當限縮,也不影響經濟實質法在稅務轄區的整體實施效果;另一方面則是借此給具有一定投資功能(其中包括股權投資)的企業留下更大的靈活空間,使其能夠減少在經濟實質測試上的合規負擔,避免對企業的相關業務進行調整。但整體而言,這個做法可能出現有違BESP行動計劃五以及新報告相關要求的結果,BVI等避稅地是否會在后續經濟實質法修訂中另行調整或者明確,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實際上不光光是我們,阿聯酋的律師同行在對阿聯酋經濟實質法的類似條款規定進行解讀時,也存在同樣的困惑。相關解讀一方面認為,“持有其他類型資產的公司將明確不是純持股實體(即使其也持有權益投資)也將不被視為從事控股業務”的表述令人疑惑不解。另一方面也認為,根據法規上下文的整體解釋,本解讀不認為公司持有其他類型的資產將自動使其不構成一個控股公司。[9]
(四)對于境外架構的影響
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實質法對于境外離岸架構的影響是長期的,因為各避稅地稅務轄區對相關實體所進行的經濟實質測試是以年度為單位重復進行的,而非一次性的判定,這實際上是對企業的實質性以及持續性合規遵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畢竟企業在存續期間可以隨時轉換經營從事不同類型的活動,這些活動是否構成受規制的“相關活動”需要進行持續監管,否則經濟實質法在實踐中將很容易被規避。
以BVI為例,申報程序上,BVI公司每年都需要根據經濟實質法的規定,對其當年所從事的活動進行判定,并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后的六個月內通過代理機構向BVI涉外稅務局對其從事的核心創收活動進行報告,報告需要提交的具體文件資料與該實體的具體情形有關。例如,如果從事知識產權業務需要提交額外的支持性文件與說明,而構成其他國家居民的BVI實體需要提供相應的稅收居民證明等。值得提及的是,即使BVI相關主體未從事任何受規制的“相關活動”,也需要向BVI涉外稅務局發送告知通知,盡管目前不需要提交進一步的證明材料,但是該BVI公司是否實際合規遵從也將面臨BVI政府的持續監管。
三、我們的思考與建議
綜上,只要屬于經濟實質法項下的相關主體,無論其是否從事受經濟實質規制的“相關活動”,均會持續受到經濟實質法的管轄。考慮到相關實體從事多項業務或者持有多類資產未來可能產生的潛在判定義務與可能的證明責任,我們倒傾向于認為,如果僅僅是純控股公司,不應刻意投資其他類型資產以試圖免受經濟實質法的規制,畢竟作為持股平臺,簡化經濟實質測試在實踐中已經是很容易被滿足的。既然能夠對此合規遵從,也就不必擔心不遵從經濟實質法所帶來的的法律責任。但退一步說,如果確實存在不同業務安排、投資組合和復雜的資產持有結構(例如存在信托安排),那么真的需要站在全局資產布局的角度,認真思考經濟實質法所帶來的影響(對境外的相關交易安排的稅務規劃),以及對于相關實體合規遵從的長期性與實質性要求。
腳注:
[1]參見關于廈門東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并在創業板上市之補充法律意見書(一),http: //reportdocs.static.szse.cn/UpFiles/rasinfodisc/RAS_0001749239C8503FE0D926CF140C553F.pdf
[2]http: //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s/action5/
[3]https: //www.oecd.org/tax/beps/resumption-of-application-of-substantial-activities-factor.pdf
[4]參見Ensuring compliance, OECD, Resumption of Application of Substantial Activities Factor to No or only Nominal Tax Jurisdictions, p15, http: //www.oecd.org/tax/beps/resumption-of-application-of-substantial-activities-factor.pdf
[5]參見Substantial activity requirement in the context of non-IP regimes, OECD/G20 BEPS Project Action5:2015 Final Report, p39, https: //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241190-en.pdf?expires=1601261002&id=id&accname=guest&checksum=EB7E4CA05FDD5259E33FACD699D0F760
[6]參見百慕大《2018年經濟實質法》第2條定義中對“控股實體”的表述,“‘holding entity’ may include a pure equity holding entity.”
[7]所謂簡化經濟實質測試(reduced economic substance)指的是通過較少的測試要求即可被認定具備經濟實質。具體而言,僅需要:(1)遵從BVI商業公司法或者有限合伙法的成文法規定以及具備充足的雇員和場所消極持有或者主動管理持有的權益投資。根據《經濟實質規則》第8.2條的規定,純控股實體聘用當地代理以及利用代理所提供的服務,也可以用來滿足簡化經濟實質的要求。
[8]以BVI為例,參見BVI《2018年經濟實質法》第2條定義中對“控股業務”的表述,“‘holding business’ means a pure equity holding entity.”
[9]http: //afridi-angell.com/items/limg/c_406UAE%20Ministry%20of%20Finance%20Issues%20Guidance%20on%20Economic%20Substance%20Regulations.pdf